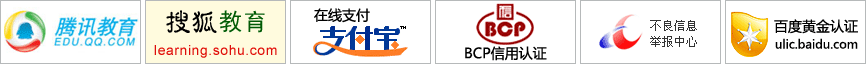【摘要】文章对“家国观念”的界定及其演变进行梳理,然后阐释了张爱玲作品中的家国观念的表现,包括:家与家族经验叙事、对住所与故乡的眷恋和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张爱玲;家国观念;表现
在文学研究界,最初给予张爱玲极高评价的是文学史家夏志清,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张爱玲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热爱中国文化,认为张爱玲是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1]。从这点上看,张爱玲及其作品蕴含了中国现代主流作家的“感时忧国”因素。在这之后,黄修己在《张爱玲名作欣赏》中解读她的《中国的日夜》时,认为张的爱国情感是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2]。池上贞子在“张爱玲和日本”一文中认为张的脑海深处永远是中国,也正因为她的这种思想,维护了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节操和荣誉。阎纯德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中,论及张爱玲时提到她是一个走过乱世的爱国者[3]。虽然以上学者没有就“张爱玲是爱国的”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也因此激发了我对张爱玲家国观念的研究兴趣。张爱玲是否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家国观念”?如果有,这些意识在她的作品中是怎样表现的?这是我的论文将要探讨的。
一、“家国观念”的界定及其演变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家国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上看,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结构的因素,家国观念就是“家国同构”。
“家国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发生演变,在战乱与朝代更替期间尤为明显:春秋战国、两晋之际、唐末、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等不同时期,人们的忠君爱国是有所不同的。古代中国人的“家国观念”是建立在忠于和服从于某一君主家庭为基础上的,并以此达到维护自身和家族利益的爱国。
到了近现代,由于西方的侵入,中国社会呈现出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特征同原有的宗法制社会以单个的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其中存在的各种社会组织(如政治经济组织、社团、协会等)成为沟通家与国的桥梁和纽带,同时又使得现代社会的整合方式和渠道多元化[4]。
中国人传统的固有家国观念也因此发生微妙的变化,但根植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以及由此形成的“父子君臣”的“忠孝”伦理和在这伦理之下的“礼”与道德的儒家“家国同构”观念,其基因成分仍然如影随形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之中。
二、张爱玲作品中的家国观念的表现
关于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在前面已经作了较为仔细的分析与定义。那么何为张爱玲的“家国观念”及在其作品中的表现呢?笔者认为,张爱玲的家国观念及其表现是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家族)及其血缘联系的一部分,同时又蕴涵了现代性的叛逆内容。她在作品中把家国观念“无技巧”地具象化,并将其放置在文化无意识的背景之下,对于“时代”、“战争”、“政治”这样一些大的题目,有着冷静的个体式的体察。这种采用不同于主流文学表达的写作方式使张爱玲在作品中成功地跨越了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边界,从而实现了独特的文学创作。同时,她通过战争动乱的时代背景,展示了人的生存状况,这也折射了张爱玲在战争时期对文化身份焦虑所进行的另一种思考。
(一)家与家族经验叙事
国家的概念在中国自古就有家天下的传统,所以有许多学者承认“家在中国历来就是国的缩影”。“家”是人所栖居的地方,它不仅是指实体上的“家庭(家族)”及其成员,而且还可指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精神家园与民族心理,是一种文化内涵。关于文化的概念有许多解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对文化的解释是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如罗森塔尔尤金所编的《哲学小辞典》中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这就是所谓“广义的文化”,而与之相对的“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所以,文学艺术是属于精神文化范畴。所不同的是,中国现代主流文学是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具体体现在作家对家国观念的表达上,主要是对旧家庭、封建制度的否定或者是对国家社会现实政治局势的直接关注。就鲁迅而言,他是表现在国民性的研究上;就茅盾而言,他的小说人物性格的发展与政治时代大背景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张爱玲由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及其女性意识而使得她对家与时代社会的解读有着另一种的看法与表达方式。她对旧家庭与新家庭的态度是一种矛盾的心态,这充分体现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的家与家族经验叙事上。可以说,她是透过“家与家族”的视觉和家族成员的文学艺术意象化来间接地隐射出国家社会的现实状况。
张爱玲是个忠实于生活与创作的作家之一,她所创作的作品基本上离不开她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她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认为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1] 。1971年张爱玲在旧金山接受水晶先生的访问时,也曾表示她小说集《传奇》里的各篇人物和故事,大多“各有其本”。她在小说中的男女主角蓝本几乎是来自其家族的成员,其中,父亲与后母的形象及其恶劣品行出现的频率较多。被傅雷称为是其最完满并颇有《狂人日记》某些故事的风味,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小说《金锁记》中的“故事、人物,大多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2]。作者在作品中把女主人公曹七巧对其儿女幸福的破坏与人性的摧残展示得淋漓尽致。母爱是人类最崇高而伟大的,对此,“五四”时期就成名的冰心女士有过很好的阐述。但张爱玲在这里却把母爱消解、扭曲丑化呈现了疯狂而变态的令人怵目惊心的一面。笔者认为这一人物包含了她曾外祖父家族成员“三妈妈”与其后母的影子。小说《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有她弟弟张子静的身影;而聂传庆的父亲聂介臣与后母对抽鸦片的情境则是出于张爱玲父亲的家与其舅父的家这两个满清遗老后代家庭家长的一个侧面。张爱玲创作小说《花凋》是出于对其舅父的三女儿黄家漪的哀悼,颇有为死者鸣不平、谴责封建遗老遗少的味道,但由于批判得太入骨而使她的舅父感到不快与不解,并对她由爱(爱护)生恨。
生活中的后母给张爱玲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创伤,所以她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喜相逢》、《无语问苍天》、《星星、月亮、太阳》、《早生贵子》等剧本出现的后母都是负面的。而1963年她发表的剧本《小女儿》中的后母形象则是温柔、慈祥、包容的,这是蕴含了她深刻的生命印迹。当时她正和赖雅结合,成为赖雅子女年轻的后母。而剧中的后母与孩子间的误解是在相互理解与体谅的情感下得到化解的,这表现了张爱玲对完满家庭的渴望[3]。如果说曹雪芹、鲁迅、巴金等大作家以家(家族)为题材的写作是反封建社会礼教的一种重要方式,那么张爱玲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面临封建伦理关系崩溃的情景,她用文学的艺术手法毫不留情地把其家庭、家族经验及其家庭成员生活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如在遗老、遗少家庭的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那些病态的人,病态的事)真实地描绘出来,也是属于反封建反传统特质的,与家国观念表达强烈的作家产生异曲同工之妙。
(二)对住所与故乡的眷恋
故乡题材是现代文学的主题之一。以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乡土小说为例,在鲁迅乡土小说的启发和影响下,许多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未名社等一批远离故乡、侨寓城市的文学工作者(中国自古以来的大部分人口是生活在乡村或城镇的环境里,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也基本上是出自其中。更有意味的是这些作家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南方乡镇,所以山清水秀、夕阳时分炊烟袅袅便是他们家乡风景的常见的画面),怀着乡愁(思乡)思绪,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眼光来审视今昔、城乡、传统现代、先进落后。他们重新回顾与整理自幼熟悉的故乡农村或小镇生活的记忆,用抒情写意的笔触,描画出乡间的泥土气息、地方色彩和人们的风俗习惯与生活特征,这是乡土作家展示的离乡思乡之情,小说中的人物活动空间往往带有想象与美化性质的乡村美丽的自然风景(如废名、沈从文笔下的牧歌般的农村意境);或以客观写实的笔法反映还乡后的故乡在中国政局动荡的情势之下日益趋于破败、落后、停滞的情景,以达到揭示落后、愚昧的启蒙意义或表达人事变迁的感慨,有较强的批判国民性与唤起民众革命的社会意识(如鲁迅的小说《故乡》。这也是乡土小说家与“左翼”作家最突出的写作特点。);或者以宏大的叙事为背景着力揭示中国农村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如茅盾的农村小说)。这些小说的内容主要是描写中国乡村社会宗法制的基本形态和乡村人们的生存状况。因此,“故乡”题材,以乡村文化和风俗人情作为文学审美对象的地位和价值在现代文学史上居于主流地位[1]。在这一意识观念的影响之下,人们的心目中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故乡就是有山有水有蓝天白云或者是破败的田园景象。其实确切地说,这是从乡镇走出来的文人们的家乡,是属于中国大多数人们的家乡,是很富有诗情画意的、有泥土气息的和有待进一步现代化的人文乡土。
而对于城里人的故乡,那是怎样的呢?作为成长在大城市上海里的满清遗少没落家庭的作家兼市民的张爱玲对故乡的把握与理解能否成为城里人的故乡情结的代表呢?关于故乡的概念,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这样解释道:“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家乡;老家”。于张爱玲而言,故乡就如其在散文《道路以目》中描述那样:“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搧出滚滚的白烟。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寒冷的天气同“人、火炉、白烟”,还有黄昏时分的人力车、挽着网袋的女人、小饭铺形成一组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市民的一个生活画面,张爱玲就是喜欢这个有人气有暖意的和带着人情味的(她为“绿衣邮差骑着车载着其母亲”的情景而感动)上海故乡。她对于她的住所“公寓”的描写也充满了人间味。如开电梯的中国人闲暇的时候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菜烙饼吃;她家对过的一家仆欧,一面熨衣服一面将电话里的对话译成德文给东家听;楼底下的俄国人在教日文;二楼有弹钢琴的;闻到了煨牛肉汤与泡焦三仙的气味。这公寓里的一幕幕(每一家的“秘密”)在炎热的夏日里随着大门的敞开而暴露无遗,但是谁也碍不着谁,各做各的,各享其乐。这是住公寓的较之住乡村的好处,即使春光乍现也不会如在乡下一样遭到闲言秽语。这是中西方文化杂糅的一所公寓,是张爱玲的居所,她爱这样热腾腾的人气和热闹的市声,她可以伴着电车的声音入睡。这同有诗意的文人在乡间听着蛙声、松涛、海啸入梦一样的有情趣。
张爱玲对中国(家)的情感其实是深厚的,她的散文《诗与胡说》中的一语,“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别人的金窝银窝(外国)固然好,但是自家(中国)“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张爱玲喜欢“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1]这便是张爱玲的对家与故乡的眷念。
张爱玲的这种怀乡情绪在其人生的后期表现得更加的浓烈,如她倾心于《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国故的整理与研究。她七十岁时创作的散文《草炉饼》是她在看了大陆小说《八千岁》而作的篇什,在文中她还是从细致的日常生活着手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怀乡之情,她惦记着上海的“草炉饼”,就像周作人怀念“故乡的野菜”,梁实秋回味着“金华的火腿”。
(三)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同
张爱玲喜欢中国的文化,具体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与对中国民俗风俗及事物的喜爱上。
1、在创作上,她承袭了中国古代小说传奇志怪和故事的传统兼吸收了《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国故的写作特点:注重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刻画,对服饰尤其是对传统服饰的描写非常的细致,关注家族、人性、性爱与环境的关系描写,使得她的作品具有中华古意的韵味而耐人寻味。
2、在个人情趣上,张爱玲从小喜欢阅读中国传统的小说,她还喜欢素描画,对音乐也情有独钟。她在《谈音乐》中,以门外汉的眼光把西方与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音乐谈论了一番。她把西洋的凡哑林(violin)同胡琴比较,把把西洋的交响乐同中国的锣鼓声比较,发现自己喜欢的是后者。她认为胡琴与锣鼓声有人间味、也较自然,没有刻意的雕琢,符合中国人的人情。锣鼓的敲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地打来,再吵我也能够忍受”,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而由凡哑林与钢琴弹奏的交响乐是刻意的安排,紧密与复杂的攻势则令其畏怕。她除了对中西音乐进行对比外,她还把中西音乐作各自的对比。在比较了中国的通俗音乐的大鼓书、弹词与申曲之后,她得出结论:认为申曲“最为老实恳切”,充满了人间味,所以她喜欢申曲。
3、在人性人情方面,张爱玲认同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她善于在中国人复杂的伦理情结中发掘出人性的善与恶。如她后期的剧本《小儿女》中就以中国人传统的温厚、宽容的良善面来解决不完美家庭的危机。至于对人性恶的一面,则在她的小说中有充分的表现,有为了金钱而不惜戕害其儿女幸福与自己爱情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有为了个人的利益、想攀升至上层社会而牺牲自己女儿幸福的《琉璃瓦》中的姚先生;而《花凋》中郑川嫦之死则不仅是出于其父母亲与姐姐们的自私而且还出于其本人情感脆弱的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堕落则是经不起其姑姑梁太太的诱惑。张爱玲在她的传奇小说中把“人性恶”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毛骨悚然,有力地批判了中国人的人性,颇具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特点。
关于中国的城市文明,张爱玲比较喜欢充满世俗的市民日常生活趣味的画面,因为几千年的文化精髓与历史的轨迹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延续获得新的生命。无论何时阅读张爱玲的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不禁令人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街道富有生活气息的一幕:那时上海的街道间的空中是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街面的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播放着梅兰芳的戏曲;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嚷卖着癞疥疮药;而‘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是酒店。而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张爱玲对自己买臭豆腐情景的描写可谓是神来之笔惟妙惟肖:一听卖臭豆腐干的来了,便立即抓起一只碗,急奔楼梯跟踪前往,直到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之后才再乘电梯回屋。这些富有市民生活气息的都市情节是张爱玲所流连忘返的中国城市市民文化,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城镇文明的一个体现。所以张爱玲对承载历史的平民大众有着特殊的情感。
总之,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具有雅与俗、古代与现代等独特性与多面性的文化特征,这同时也体现了她的家国观念的基本特征。她对中国的情感是从文化的层次出发,她个人的情感婚姻同其文学创作一样,是矛盾而复杂的;给人一种如镜花水月般的迷乱镜像,容易产生歧义的现象,而歧义恰是文学文字的特点所在。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情结与传统的中国女性意识,她关心普通人(小市民)的生活和人性,对没落的中产或大富的封建贵族既怨恨又同情(如她对《儿女英雄传》中的“旧家庭的专制”感到“愤愤不平”的同时又对封建专制的统治者“安老爷”表示同情)。她没有加入革命战争与关注国家命运的宏大题材创作,而是以其独特的女性意识从爱情婚姻家庭的中国日常生活入手,反映中国伦理道德的悖论,同时隐隐地流露出对在革命战争年代下的平民性格的现代性评判与同情。此外,张的家国观念对后人的影响也是极具争议性的,这种争议主要是在于人性(尤其是人的身份认同)同民族、时代、革命战争乃至改革的不相协调上。关于这一点,人性如何能和谐地同时代潮流同步似乎成了中国人尤其是社会问题研究者、改革家们有待深思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李欧梵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7月初版。
[3]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1版。
[4]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5]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6]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7]蔡凤仪:《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台北皇冠文学出版公司出版,1996年3月第1版。
[8]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5年11月初版。
[9]吴著斌:《论张爱玲作品中的历史意识》,载《黄石教育学院学报》第23卷,第4期,2006年12月。
[10]陈碧红:《论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第20卷,第4期,2005年4月。
[11]姚晓雷:《民间,一个演绎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范畴》,见《世纪末的文学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