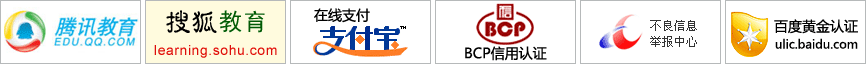很多书籍和评论都承认,《金锁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金锁记》发表不久后,傅雷就曾著文加以评论,认为是“我们文坛最美收获之一”,也是张爱玲的巅峰之作。
张爱玲小说创作总是在探讨女性与金钱的关系,为了自己的生存或是摆脱贫困,把自己的婚姻作为唯一筹码,以金钱为最终归宿,用青春去赌未来,结果只能是输掉青春,输掉爱情,输掉了人格,甚至以所谓的亲情作为代价,最后只能在生命的角斗场上赢回一点万恶金钱。
同样,这部小说也讲述的是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子曹七巧,因为哥嫂贪财,将其嫁入大户人家,做了一个残废人的妻子,在等级森严的旧式家庭中消磨了青春,从而丧失了做人的意义和尊严。《金锁记》侧重点不在于控诉旧式婚姻与宗法家庭的残酷,也没有对曹七巧大洒同情之泪,但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新视角。
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所刻画的是不幸的婚姻导致了一个女人怎样的心理变化,或者说,显示的是缺憾怎样激发出了一个女人内心的阴暗面。
《金锁记》以一种回忆性的时间气氛开始了整个故事: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人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 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9]
年轻人和老年人眼里的月亮并不一样,然而老年人也曾经年轻过,年轻人也会渐渐变老,不变的是那温暖而又冷清地注视着我们的月亮。一切都发生在这个恒久不变的既温暖又冷清的月光下。
紧接着月光照进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鬟凤萧的枕边,引出了小说的第一个具体场面,通过丫头间的对话侧写曹七巧。
连丫头都敢这么歧视少奶奶,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信息,这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女人,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因此语言低俗,还有一些手脚不干净的亲戚,即使是当上了豪门的少奶奶,那也是永远的麻雀,加上一个残疾的丈夫,这就出现了一个完全没有地位,而又令人生厌的少奶奶形象。
第二天早上曹七巧正式出场。
众人低声说笑,榴喜打起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
兰仙云泽起身让座,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颇有《红楼梦》凤姐出场的笔法,前面做了不少铺垫,骤然出现,立即成为众人焦点,动作、姿态、言词,都透着与众不同的风格,用这种夸张的装饰来聚焦视线[1]只不过,凤姐令人生畏,而七巧只是令人生厌而已。可又正式这种爱出风头的夸张气焰,透视到她极度自卑的心理。
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叫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
本来请安已经是迟到了的,一进屋来,最先也没有请不是,而又借机把自己的悲惨处境当众赤裸裸的抱怨了一遍,更是把自己的地位贬得一文不值,这是一种弱者的自卫心理,想要得到同情,得到谅解,相反得到的是所有人厌恶和漠视的眼光。而这一整天发生的事全是琐屑的,对于小姑的隐私表现的过度关心,并在婆婆面前搬弄小姑的是非,惹得小姑痛苦;与小叔子姜季泽之间的调情,季泽的怯弱;正好她哥嫂来探访,引起她满腹心事及身世之感,冲哥哥发了一顿脾气,最后还是送了一大堆东西给他们,少不了财大气粗的架势。
这几个细节实际上浓缩了七巧结婚十年间的全部日常 生活。缺乏肉体的关爱,缺乏内心的交流,同一屋檐下的人在礼法的控制下井然有序,却相互隔膜,每天都是怨言,算计,闲聊,中伤,当生命的感觉刚刚涌现,现世的规则便会将它击退粉碎。
十年过去了,这样的时间仿佛漫长而又短促,七巧终于变成了寡妇,婆婆也去世了,接下来就是分家,也学是期盼这一天的到来,才一直支撑着。
今天是她到姜家来之后一起幻想的集中点。这些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11]
她所牺牲的一切,将会在今天通过分家而得到补偿,她以为对于财富的占有能够弥补她曾经失去的一切,她不知道,那些永远逝去的是回不来的,也没有办法而已弥补的,她只是把缺憾的情感转移到她所可以得到的金钱上来,这一切,她到死都不明白。
分家时,任性的贪婪和自私往往暴露无遗。在利益的诱惑之下,血缘的联结会变得十分薄弱。金钱建造了华丽的宫殿,也建造了荒凉的人性沙漠。[2]七巧不顾一切的为自己争取该得到的,然而,“还是无声无息的分了家,孤儿寡妇还是被欺负了。”但毕竟是有了自己的家,完全只属于自己的 财富。
分家后的几个月,姜季泽在七巧家里出现,同事也带来了她的爱情,然而,对于金钱的欲望,攫取与守住的冲动,七巧最终还是亲手毁了这本来可以属于她的爱情。七巧巧妙的揭穿了季泽想借男女之情来获得金钱的动机,便暴怒地赶走了季泽: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都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站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12]
在这里,她在抉择时的心理波动曲折幽深。她不仅为自己困惑,为她自己服从于“情欲”还是“物语”感到困惑,更对男女之前的真伪感到迷惑。在那一刹那的“激情”与
“压抑”之中,凸显了七巧一生的悲剧:永远丧失了一个女人最应该拥有的爱与性,物的占有欲淹没了生命的欲望。就这样,七巧见见与现实失去了联系,接下来的画面都在围绕儿子长山,女儿长安的感情纠葛。她的魔妇形象从这时候开始渐渐鲜明。
侄子与长安玩耍却能引起她的愤怒与疑忌,用恶毒的语言中伤侮辱侄子一家,气得侄子“卷了铺盖,离开了姜家的门”,没有一丝愧疚的七巧反而在屋里以母亲的身份教导了一番长安,并心血来潮帮长安裹脚。
只是因为长安在学校丢失了一些衣服,七巧便要到校长那里讨公道,仅仅因为害怕出丑的长安因此放弃喜欢的学校和喜欢她的老师同学,告别学校的少女长安,更永别了她所有的理想,闲在家里,举止越来越像她的母亲。
儿子长山的婚姻因为她的介入和恋子情节一再的被毁灭。与新媳妇关系紧张,以窥探儿子房事为乐,缠着儿子不让儿子回房去接触媳妇,更在亲家面前公开儿子媳妇房事细节,使得亲家落荒而逃,最终葬送了儿子的幸福和媳妇的生命。
遇到真爱童世肪的长安遭到七巧的嫉妒,受到母亲的诅咒,被迫牺牲爱情,但却又藕断丝连,于是七巧设宴彻底断了长安与童世肪的联系。
最后“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迷蒙的回想了自己的一生,她知道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子女都恨她,知道她用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只剩下半条命,冷静下来的她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
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嫁之后的几年,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搞搞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异地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13]
肉体的枯萎表征着生命意义的中介。蓦然回首,才想起,无论任何时候任何人,只能选择一个方向奔走到底,也自然只能体验到那一种别样滋味。[3]人类的行动也被这样的体验滋味所牵引着,人的命运也因此被主宰着,毁灭着自己,也会毁灭着别人,而别人也毁灭着别人,就这样永远停留在自我毁灭或相互毁灭的循环体中。
七巧人格分裂的过程是她的尊严地位以及情欲和社会、与他人不断斗争的结果,社会旧事物的腐朽和她要强的性格共同毁灭着她,走向人性最丑恶的一面必然是她最后的归宿。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为什么毁灭必然是她的最后的结局:
客观因素:社会旧思想旧观念与历史的摧残。
在世界性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后,中国人仍然沉浸在落日的余晖里,做着世界强国的春秋大梦。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惊醒他们不觉晓的春梦。作为中国最商业化的上海,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封建腐朽的陈旧观念与西方的拜金主义在上海这个大染坊中融合,沉淀,这便构成了《金锁记》的社会大背景,也便杂交出了“曹七巧”这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与“怪胎”。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七巧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的腐朽、病态的、霉变的社会环境里,旧的传统思想并仍然苟延残喘。在这样僵化的、封闭的空间里,“存天理,灭人性”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主宰人的命运。 就像列宁说的,“所有的东西——不光是土地,甚至连人的劳动、人的个性,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出卖的东西”,从而形成了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交织的畸形现象:一方面,封建家庭关系、伦理规范日趋瓦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里与封建残余产生化学效应,达到本质上的相同——贪欲和极端的利己主义,人的心灵被蛀噬、被毒化,沦为黄金枷锁下的奴隶与怪胎。就像七巧说的“表格虽不是外人,天 下男子都一样混账。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学费总得想法子拿回来,便宜了他们不成?”;“早不嫁,迟不嫁,偏赶着这两年钱不凑手。”[16]一切都已金钱为前提,除了金钱,爱情、亲情对她来说都不值一提。这是七巧变态心理的巅峰期。
由此可见,在曹七巧身上,有着浓厚的拜金主义色彩,她才会感叹:“人是靠不住的,靠的住的只有钱。”其次,她的悲剧与不幸主要是由她残缺的婚姻体现的。在封建社会,婚嫁讲究门第,地位也分正庶。曹七巧仅是一个麻油点的女儿,出身卑鄙低微,家境贫寒。而姜家呢,是达官显贵,家财万贯,声名显赫。在资产阶级婚配注重金钱大背景中,她与姜家二少爷的结合,冥冥中就种下了命运的苦果,注定是一出悲苦、苍凉的结局。“这屋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往她头上踩”,可见七巧遇到了何等的轻视与凌辱,姜公馆的门第又是何等森严!正如七巧哭诉的那样:“上上下下谁不是势利的,狗眼看人低。”连下人们也瞧不起她,说她是“麻油店的活招牌”。门第观念使人的尊严、人性被践踏,被扼杀。就连曹七巧也被门第通话了,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如“趁早别自己骗自了,姓童的还不是看上了姜家的门第”。
再有,中国传统道德中“一女不事二夫”的贞洁观念,扼杀了无数青年寡妇的命运,七巧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中国男性似乎在性爱的问题上有着疯狂的施虐倾向,以及极端的占有欲。这种对于“贞操”的疯狂迷恋,显示出中国男子的怯懦与自私。将贞操视为占有的标志,同时,又以贞操为枷锁,锁住了成千上万颗悸动的心。然而,中国有着一套动听,神圣的思想体系,几千年融进了民族的血液,成为常识,规范着女性的言行。最典型的“三从四德”,这些观念的目的都是为了压制妇女身心的开放和发展,剥夺他们享受,体验生命的权利。妇女完全成为物品或财产,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独立品格。从心理学分析,欲望是无法消失的,只能转化,只能转化为其他行为,才能获得平衡。而这种转化往往因为压抑,而具有乖戾之气[13]。
所以,假如存在一个寡妇原形系统,七巧无疑是这个原型的现代翻版。作为寡妇的七巧有着这种原型固有的素质,但也有着另外一下东西,几乎无法用“寡妇”这个词曲概括。
除了残缺的婚姻,七巧身上还有这浓重的封建因素,对女儿长白说:“按说你几年十三了,裹脚已经嫌晚了,原怪我耽误了你。马上这就替你裹起来,也还来得及。”又如:“七巧低声道:‘我打你这不孝的奴才!打儿时变得不孝了?’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累,公侯将相的,其实全部是那么一回事!早就外强中干了,这两年连空架子也撑不起来了。人呢,一代坏似一代,眼里哪还有天地君亲?”这些都是造成她注定 要走向灭亡的不可或缺因素。
主观因素:七巧本身潜在的变态心理。
夏志清说:七巧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
一个健康的女人,应当像张爱玲所说的,“强壮,安静,肉感,皮肤新鲜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作为一个寡妇,曹七巧的女人性被极度压抑。然而,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七巧,只是回忆中的朦胧影象,似真似幻。小说中只有两次让人见到青春的七巧,一次是因为她哥嫂的到访,勾起了她的回忆,另一次是在临终前的回忆,从前也有过滚圆的胳膊,也有过喜欢她的青年男子。少女时代的充实,幻想,活力早已经成为过去。一旦嫁入姜家,她便一天天的枯涸了。与“没有生命的肉体”相伴,她自己也成了行尸走肉。她嫂子的话从侧面透露了一点消息:
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换了个人?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嘴头子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虽是比以前暴躁写,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得人心的地方.[14]
在丈夫去世前,七巧的言行已充满着性压抑的焦躁,紧张,谈话的指向总是不由自主的滑向性爱方面。还毫无顾忌的向别人抱怨自己的丈夫,对他们的妯娌们说:“知道你们 都是清门静户的小姐,你倒是跟我换一换试试,只怕你一个晚上也过不惯。”对小叔子季泽更是直言不讳:
“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想人的脚又是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
“天啊,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姿是多好的……多好的。”.[15]
毫无掩饰的言辞,流露出对于健康肉体的渴望。
不仅说,而且有所行动。七巧热切的撩拨小叔子,却遭到拒绝。七巧只好在打探小姑的心事,把弄是非之类的琐事中,发泄她过剩的精力。犹如一头困兽,被老式的清规戒律捆绑着。七巧医生中,季泽是最有可能使她成为“女人”,使她的情欲得到适当的宣泄。然后他究竟放弃这唯一的一次可能的性爱,因为季泽只不过想骗她的钱。
季泽当年拒绝她,是因为不想自己自己的名誉受损,同时,也无法承担对于“二哥”的良心负担;七巧现在拒绝她是因为想守住自己的家产。两人的心里全是自私。
在一个自私的人世,人要想得到爱情,就得装糊涂,得容忍相互的“坏”。
虽然张爱玲写到:“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 吧……她要他,就得装糊涂……人生在世,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归根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可是张爱玲自己却没有像写的那么旷达,她内心明镜一般,也和七巧一样装不了糊涂。 [5]
七巧过于清醒,因此还得忍受欲望的煎熬。她变得越来越怪诞;儿子娶了媳妇,她居然要求儿子描述闺中隐秘,又津津有味地向别人转述,弄得媳妇人不人,鬼不鬼,终究抑郁而死
女儿有了男朋友,她又处处为难,恶言相向,还设计破坏,终于还是将长安的姻缘毁灭了。
行的压抑导致七巧丧失了作为母亲的天性,出现了种种歇斯底里的变态行为。但是把七巧的形象框定在“寡妇”的界域,并以为她的一切怪异,疯狂并完全源于对性的压抑缺乏充分的根据,也体现不出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深意。
七巧满心骚动着强烈的委屈感,除了上述性压抑之外,还与她的出身有关。因为出身低下,连丫鬟都瞧不起她,“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瞧不起她”,在这么一个势利的世界里,七巧感到无形的敌意包围着她,这个世界处处与她过不去,她见到的人似乎都过得比她好,唯独她最最不幸。她的语调间潜藏着对被理解,被同情的向往,她习惯于以弱 者的姿态来自卫,宣泄。而人在极致的情势下,最容易现出本性。[6]
她一出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充满火药味:“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竟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弱者的委屈,不满,引致的是对这个世界与人性的怀疑,乃至敌视,这是七巧形象最令人战栗的光彩。
七巧的形象其实暗示了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孤立的,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受害者,每一个人都处在深深地不安之中。细想,每个人的内心也时常会浮现出七巧们的气息,压抑、不满、敌意、自卫、毁坏等等破坏性的心理潜流,像一条暗涌潜伏在人性的深处,随时爆发,一发即不可收拾,只不过我们会用理智化解它,不让他肆无忌惮的流淌延续下去。
因此,曹七巧这个人物形象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一个反面形象,也不是一个正面形象,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一种宿命的,身不由自的存在。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金锁记》就是将原本美好的人在现实的终极残害下如何一步步走向毁灭展示出来。于是有人言,“‘她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 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归宿所在,她以否定现代生态下的女性女奴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地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诸般枷锁和桎梏” [7] 。就仅用了短短的两万多字,就能把一个女人一生的经历与心理变化过程细腻而跌宕的呈现出来,这无可挑剔的表现力与现代汉语的运作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文坛最伟大最美的收获。
结论
张爱玲对《金锁记》曹七巧的塑造向世人证明了她能够一直以来乃至现在活跃于文坛不是偶然。她的才情,她的天份,是不可仿造的一个“奇迹”。于青这样说道:“当她肚子在美国隐士般谢世后,人们这样称赞她的作品: 堪为一个王朝的结束。”[8]再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张爱玲这样拥有巨大的魔力,让千万读者悲苦泣笑于她营造的文字之间,痴迷于她的作品她的传奇,与她“亲密接触”,深深地被她的魅力所感染,也着实让我变成了“张迷”。这是此次论文的最大收获。
参考文献目录:
[1] [6]司美娟:《张爱玲传奇》 〔M〕,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12。
[2]西岭雪 :《寻找张爱玲》〔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09。
[3] [7] [8]于 清:《张爱玲》 〔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07。
[4] [5]玮 清:《女生张爱玲》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01。
[9] [10] [11] [12] [13] [14] [15] [16]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选》〔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03。